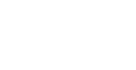JN江南·(中国区)体育官方网站-JN SPORTS格陵兰岛:包袱变身香饽饽
2025-08-23 15:31
2024年11月首府努克的新机场修好之前,格陵兰最大的机场在一个叫Kangerussuaq的地方,这里原先一个人都没有,也没有公路通往其他城镇。数十年来,格陵兰人习惯了先从各个定居点飞到这个航空枢纽,再转机去努克、丹麦本土或其他国家。而踏访的外国游客往往也很纳闷,为什么格陵兰人要把枢纽修在一个杳无人烟的地方。
“太多人问我这个问题!”在驱车前往格陵兰冰盖的路上,向导谢尔·温特(Kjeld Winther)哈哈大笑,“因为这个机场是美国人修的。”
事情要追溯到二战期间,丹麦本土被纳粹德国占领后,丹麦的领地格陵兰成了距美国本土最近的“敌国领土”。这下急坏了美国人,为了防止德国人以格陵兰为据点袭击美国本土,1941年4月9日,时任美国国务卿赫尔(Cordell Hull)与已宣称不听命于丹麦占领政府的丹麦驻美大使考夫曼(Henrik Kauffmann)签署了《格陵兰防御协定》(Agreement Relating to the Defense of Greenland),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。一两年内,美军就在Kangerussuaq建立了岛上最大的机场。又在1951年于格陵兰岛的北部建立了图勒空军基地(现名皮图菲克太空军基地,Pituffik Space Base),就是2025年3月美国副总统万斯造访的那个。
在荒无人烟的冰天雪地修建机场自然靡费不菲,但此事毕竟关系到美国本土安危,多花点钱也不在线年开始,美军在格陵兰西部一条180公里长的峡湾深处(Kangerussuaq在格陵兰语中的含义正是“长峡湾”)修建了这个大型军事机场。这里靠着海边,方便运送物资,又位处峡湾深处,相对风暴较小,适合飞机起落,便成了美军的第一选择。这里不靠近任何城镇,当然这也并不重要,本来这座机场也不是用来服务格陵兰人的。
二战的硝烟刚刚散去,冷战的铁幕就已落下。1950年代,作为美国本土与欧洲北部的“中点”,Kangerussuaq成为美军跨洋航线的加油与中转站。美军在这里部署数千名士兵,配备了雷达和气象观测设备,把这里定位成对苏“第二防御链”的一部分。跑道也被延长至2800米,可以起降747等宽体客机,迄今仍是整个格陵兰最长的飞机跑道。
上世纪50年代,民航业开始发展,受当时技术限制,5000公里以上的跨洲航行需要中途加油。像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(Anchorage)一样,改成军民两用机场的Kangerussuaq也成了知名的“中转加油点”。1954年,北欧航空(SAS)开通了全球首条跨越北极的航线,从哥本哈根经停Kangerussuaq飞往洛杉矶。开通航线时,他们设立了一块“世界方向标”,展示Kangerussuaq前往世界各地目的地的旅行和飞行时间。当时“世界方向标”还没有像如今这样哪都有,因此也成为跨洋旅客合影的首选之一。那些年,许多欧美游客对格陵兰的最深刻印象,就是这个“世界方向标”。
冷战结束后,美军撤走了。随着喷气式飞机的普及,跨洋航线也不用来加油了。要不是岛内中转的需要,Kangerussuaq恐怕就被废弃了。为了维持机场和城镇发展,当地利用离冰盖较近的优势,推出“冰盖体验一日游”:乘越野车前往冰盖边缘,在冰盖上进行短途徒步。全世界冰川有很多,冰盖可只有两块:南极冰盖和格陵兰冰盖,Kangerussuaq被包装为“进入世界第二大冰盖的门户”。
冰盖体验花费约800元人民币,包饮品、饼干和往返交通,是格陵兰最便宜的旅游项目之一。离开机场后,很快就没了手机信号,温特开着一辆由卡车改装而成的大巴,带我们在一条碎石路上前往30公里外的冰盖边缘。这条路2001年建成,由德国大众汽车出钱修建,为的是测试车辆在极寒环境下的表现。2004年大众汽车撤离后,这条公路被当地政府接管,成为通往冰盖的必经之路。
抵达目的地,穿上冰爪、拿上登山杖,我随着温特的脚步走上冰盖,走了不到一公里,脚下的冰盖厚度已达数十米。这块冰盖相当于压在格陵兰岛上的一块大冰疙瘩,覆盖了全岛面积的80%,越往中间越厚。在岛的中部,冰盖最厚处达到3200米——你甚至可能有高原反应。谈及特朗普对格陵兰的觊觎,温特嗤之以鼻:“他可能是在地图上看到这里显得面积很大,所以动心了吧?”
早在第一个总统任期,特朗普就表现出对这个第一大岛的浓厚兴趣。据《分裂者:特朗普在白宫,2017-2021》一书透露,“买岛”的想法最初在2019年前后由美国雅诗兰黛集团的老板罗纳德·兰黛(Ronald Lauder)提出建议,特朗普受到启发后持续推进,并要求时任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(John Bolton)进行可行性研究,甚至考虑用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“交换”格陵兰。为了推进此事,美国重开了在努克的领事馆。
格陵兰的面积不到美国本土的1/4,然而由于纬度很高,在“墨卡托投影”下,其在平面世界地图上显得尤为庞大,甚至比整个美国本土看着都大。或许当特朗普的目光投向世界地图时,这片巨大的领土吸引了他的目光?他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:“我喜欢地图。我总是说:‘看看这幅图。它(格陵兰)很大。那应该是美国的一部分。’”
美国喜欢买领土倒不是新闻,甚至连找丹麦买地都不是第一次了——1917年,美国就花了2500万美元买下丹麦在西印度群岛上的殖民地,并将其更名为美属维尔京群岛。然而百年过去,国土买卖早已不再流行。博尔顿硬着头皮前往哥本哈根与丹麦政府进行私下协商,却被一口回绝。两国关系一度紧张,特朗普还取消了访问丹麦的行程。不过他的野心并没有打消。4年之后,在他再次入住白宫前后,他再次提出“购岛”设想,这次的理由是:稀土!
“看看这里,离海边不到30公里,冰盖厚度已经有二十多米,”温特踩了踩脚下的冰面,“稀土覆盖在这样的冰盖之下,开采出来要花多少钱?肯定是赔本买卖!”
丹麦-格陵兰地质调查局高级顾问托马斯·瓦明(Thomas Varming)从专业的角度诠释了为何在格陵兰开采稀土不靠谱。他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,开采稀土矿物相对容易,而真正的挑战在于加工。由于化学性质相似,这些稀土元素的提取和分离非常困难。此外,格陵兰缺乏基础设施,矿区远离村庄或城市,这意味着需要考虑建设港口、住房、能源和供水、污水处理系统以及机场来容纳矿场的工人。而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。此外,这里严酷的冬季气候使企业运营时间大幅缩短。“要使这些矿物成为格陵兰岛重要的收入来源,原材料的价格必须上涨,因为目前开采这些矿物的利润还远远不够。”
无论如何,特朗普最近很少再提格陵兰了,也许他的目光已经放到了其他更容易取得稀土的国家,比如乌克兰。当然,没有人知道,当他有朝一日把目光再投向世界地图,会不会再对这个地图上方的大块岛屿动心。
“美国不是唯一对格陵兰动心的国家。”温特指着冰盖深处说,“挪威是另一个。滑雪横穿格陵兰冰盖,到达数百公里外的另一端,是挪威人的‘朝圣之路’。”
挪威人对“滑雪横穿格陵兰”的执念,类似于中国人“登顶珠峰”。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,当时格陵兰内陆仍是未解之谜,挪威探险家弗里乔夫·南森(Fridtjof Nansen)从无人定居的东岸出发,以“轻装快速”的方式,日行20-25公里,用时49天抵达西海岸的努克,完成了对格陵兰内陆的穿越。
南森的成功成为挪威极地探险“黄金时代”的起点,也激励了许多后来的探险家,如第一个到达南北极点的罗阿尔·阿蒙森(Roald Amundsen)。另外,19世纪末,挪威仍处于与瑞典联合的政体中,南森的壮举被视为挪威民族精神的体现,成为独立运动的象征之一。
滑这么一趟可不便宜。温特说,“25-30天的行程,大约要花15万丹麦克朗(16万元人民币)。其中的大头,是保险费用。因为如果在格陵兰腹地迷路了,是需要直升机救援的。”他告诉我,每年都会送好几拨挪威人到冰盖上,然后跟他们挥手告别。“我对他们一点都不羡慕!有这个钱干点啥不好。”
我是有点羡慕的,但我没技术、没假期,钱包也干瘪。于是他们的起点,就是我的终点。我依依不舍地坐上“卡车巴士”回到Kangerussuaq机场。
在首府努克,我发现Egede无处不在,Egede酒店、Eg江南JN体育ede教堂、格陵兰的上一任总理也姓Egede。当然,最显眼的还是在海边的一座石头山顶,竖立着的一尊雕像——Hans Egede。用丹麦语来发音的话,Egede会显得有点诡异——g不发音,d则要弱化,这个词里主要发音的是三个e,发出类似于“挨饿”的音调。不过如果用Hans Egede家乡的挪威语来发音的话,倒是显得掷地有声——埃格德。
挪威人对格陵兰的执念,可能始于他们的祖先。考古可以证实的是,公元10世纪末,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维京人到达格陵兰建立定居点,最多时,岛上有3000-5000名维京人定居。与后来以劫掠而臭名昭著的维京海盗不同,这些维京人主要以畜牧业为生,同时也捕捉海豹、海象,并与欧洲进行海象牙和毛皮贸易。
“格陵兰这个冰天雪地的岛屿为何要命名为‘绿地’(Greenland)?”在当地一家媒体工作的马萨纳·埃格德(Masaana Egede)(作者注:又是一个“埃格德”)给我讲了两个可能的原因:一是在北欧史诗《萨迦》中,传说中第一个到达这里的维京人“红胡子埃里克”(Erik the Red)在岛的南端见到了草原,于是就“绿”了这个岛;二是也有传说认为,埃里克为了忽悠其他维京人跟他一起来这里殖民定居,就给这岛起了一个“绿意盎然”的名字。
维京人来了之后不久,因纽特人也开始从加拿大北极地区向格陵兰迁徙。考古证据显示,维京人与因纽特人曾有过接触,但由于两个民族都没有留下文字记载,所以今人也无从得知他们到底是相处融洽,还是冲突频发。我们知道的是,15世纪后,随着小冰期的到来,以捕猎为生的因纽特人熬走了靠畜牧为生的维京人,成为岛上唯一的民族。维京人在格陵兰岛上的定居点痕迹,也被冰雪一点点擦去。
不过,维京人的后人并没有忘记这里。两百多年后,一个名叫汉斯·埃格德(Hans Egede)的牧师向丹麦-挪威联合王国国王腓特烈四世进言,要求来格陵兰传教。他出生于挪威北部的罗弗敦群岛,对格陵兰的兴趣源自年轻时阅读的北欧古籍与地理传说,坚信格陵兰仍存在北欧移民的后裔,并怀有强烈的传教冲动,希望将他们重新带回基督教世界。
国王批准了他的请求。1721年,35岁的汉斯·埃格德携妻子、四个孩子和几十名挪威定居者,从挪威西部港口卑尔根出发,横渡大西洋,抵达格陵兰西南部。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定居点,并给这里取名“好望城”(Godthåb, Good Hope)。而当地的因纽特人管这里叫“岬角”(Nuuk),也就是“努克”名字的由来。
事实证明,名字里带上“美好希望”并不能让一个港口风平浪静。南非的好望角是如此,格陵兰的“好望城”也是如此,这里的暴风雪如家常便饭,有时能吹得人睁不开双眼。航空业也是完全“靠天吃饭”。我买了一张前往北部旅游小镇伊卢利萨特(Ilulisaat)的机票,起飞当日被告知:航班取消,请自行去Egede酒店,由航司包吃包住,天气能飞了会有人送你们去机场。这一刻我突然有点明白,为何一段一个半小时的旅程竟要耗资五千多元人民币——里面还包含了住酒店的钱。
300年前,想来这里的天气也不会比现在更好。不过对汉斯·埃格德来说,更失望的恐怕是他未找到期待的维京人后裔。但来都来了,要是能在因纽特人中发展新教徒,也是功德一件。埃格德开始学习因纽特语言,并尝试用绘画等方式传授基督教教义。1724年,他建立了格陵兰第一所教堂和学校,教因纽特儿童基督教知识及丹麦语。因纽特人原本并没有姓,许多孩子受洗后,就跟着他姓。于是,便有了这么多姓“埃格德”的格陵兰人。
1728年,丹麦-挪威政府正式在格陵兰建立殖民行政机构,派遣官员和士兵,宣示主权,标志着近代欧洲在格陵兰的统治开始。汉斯·埃格德也被任命为格陵兰总督兼首席传教士。在贸易和宗教影响下,因纽特人生活方式发生深刻转变:传统的捕鲸与捕海豹继续存在,但因纽特人开始使用欧洲铁器、火枪和木船;教会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,基督教节日、婚姻制度和教育逐渐普及;北欧人与因纽特人通婚,产生混血群体,形成新的社会网络。
在努克,这种混杂了北欧和因纽特元素的“混搭”随处可见。城市建筑大多为北欧样式,却能看到晾在窗台和走廊上的衣裤(我在北欧从没见过);尖顶教堂旁边的海产市场里,摆放着血淋淋的海豹肉、鲸鱼肉;卖海产的小伙子,有着北欧人的白皮肤,却有着黑色的头发和眼睛……
拿破仑战争结束后,站错队的丹麦于1814年签署《基尔条约》,把挪威割让给瑞典,但格陵兰、冰岛和法罗群岛仍被保留在丹麦手中。挪威虽然心有不满,但也无力改变。直到1905年,挪威从瑞典独立后,开始强调其“维京遗产”,认为格陵兰在历史上属于挪威。爱国民众也开始跑马圈地,1931年,一批挪威人在无人的格陵兰东部建立定居点,挪威政府也“顺应民意”,宣布对格陵兰东部实行“主权占领”。官司打到海牙的常设国际法院(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),最终判决挪威败诉,格陵兰全岛领土都归属丹麦。
上世纪60年代之后,“民族自决”成了全球普遍的政治正确,丹麦也逐渐放松了对格陵兰的控制。1953年,丹麦不再将格陵兰视为殖民地;1979年,格陵兰成立自治政府,可以自行决定除外交、国防外的一切事务;2009年,格陵兰获得了“独立之门”的钥匙——“民族自决权”。也就是说,在全民公投通过的情况下,格陵兰政府可以与丹麦政府协商,经丹麦议会批准后,脱离丹麦独立。
天气转好,终于能飞了!我来到努克机场办值机,突然发现机场的标牌只有格陵兰文和英文,没有丹麦文。飞机上的广播也是格、英双语。一问才知道,丹麦语早在2009年就被“踢”出格陵兰的官方语言了。格陵兰政府的下一步计划是,发行格陵兰护照,代替目前使用的丹麦护照。
候机时坐着无聊,我便与旁边的格陵兰小哥聊天。他在格陵兰旅游局工作,此次是去伊卢利萨特出差,“那里的冰峡湾世界闻名,好多中国游客都会去看!”聊起独立的议题,这位“00后”小哥告诉我,独立已经成为格陵兰的政治正确,没有哪个格陵兰政党敢于否定独立,“前几次选举,每个政党都举出标语:我们不要做丹麦人,我们要做格陵兰人!”今年选举的标语加了一句:“也不要做美国人。”
我问:“既然这样,为什么还没独立呢?”小哥嘿嘿一笑:“差钱啊!格陵兰GDP的四分之一都是丹麦拨款补贴,独立了就没了!”
如果说殖民是原罪,那么丹麦对格陵兰肯定也是有原罪的。近年来,对丹麦殖民的控诉,在格陵兰也成为热门话题。我到伊卢利萨特机场时,候机厅的电视里在播着一档节目:一位老年女士眼含热泪在用格陵兰语愤怒地说着什么。一位乘客告诉我,她在控诉50年前丹麦政府推行所谓的“现代化”政策,强迫因纽特人搬迁离开传统聚居地,统一安置在城镇中。这种强制迁村政策摧毁了社区结构与狩猎传统,也让很多因纽特人陷入酗酒、抑郁,甚至走上绝路。
伊卢利萨特以冰峡湾而闻名于世。这里是格陵兰冰盖向海洋“输送”冰量的主要通道之一,冰川源自海拔2000米以上的格陵兰冰盖深处,当冰川推进到峡湾口时,受海水浮力作用与冰川内部压力影响,巨大的冰块从冰川前缘崩裂,形成数十米至一百米高不等的冰山。这些冰山随后从峡湾沿着拉布拉多海漂入北大西洋,成为北大西洋洋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据统计,全球约10%的冰山源自伊卢利萨特冰峡湾。在雷达尚未普及的年代,船只航行时对冰山的观测只能依靠瞭望。神出鬼没的冰山进入北大西洋后,给不少船只带来麻烦,甚至灭顶之灾,比如——泰坦尼克号。
伊卢利萨特还是探险家兼民族学家克努德·拉斯穆森(Knud Rasmussen)的故乡,这里有纪念他的博物馆和雕像。因纽特人与丹麦人的矛盾,之所以不如一些殖民地主体民族与宗主国的矛盾那么激烈,拉斯穆森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他让西方世界第一次用平视,而不是俯视的目光去注视因纽特文化。
拉斯穆森出生于1879年,他父亲是一位丹麦传教士,母亲是混血的因纽特人。他自小生活在因纽特社区中,精通格陵兰语,熟悉因纽特人的习俗、口述传统与狩猎技能。与此同时,他也在丹麦受过良好的教育,这为他成为沟通因纽特人与西方世界的桥梁奠定了基础。
在54年的人生中,拉斯穆森最著名的成就是主导了7次“图勒探险”(Thule Expeditions),重点是探索北极地区并记录因纽特文化。他的足迹遍布格陵兰、加拿大北部和阿拉斯加,通过亲身经历、田野调查和深入交流,把因纽特口述传统、神话故事和民俗完整记录下来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,种族优越感在西方国家大行其道,许多西方民族把殖民地土著民族的文化看成是低等的、不开化的,也很少有学者愿意去研究土著民族文化,放任其式微消亡。但拉斯穆森的文章和著作,让丹麦和西方世界第一次真正理解因纽特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,去关注这个极地民族的独特文化,他也因此被誉为“因纽特的荷马”。
拉斯穆森把一生献给了格陵兰文化研究和极地探险。他的去世,据说也与一种因纽特食物Kiviak有关。Kiviak的做法是选一只成年海豹,剥下皮,保留皮毛,缝合成一个袋子,塞入数百只小型海雀。放到石头堆下,密封半年到一年以完成发酵。食用时,取出海雀,用手或牙齿扯掉羽毛,吃里面的肉与内脏。听起来这是一种“黑暗料理”,然而也有其营养学意义:发酵使得食物可以保存很久,也能提供维生素C,避免因纽特人患上坏血病。不过如果制作过程中空气没有完全排出,可能滋生肉毒杆菌,那就会有烦。据记载,拉斯穆森在格陵兰进行第七次“图勒探险”期间,吃完Kiviak发生了严重的食物中毒,后又并发了肺炎。虽然队友设法将其送回丹麦救治,但最终不治去世。
无论是在伊卢利萨特还是在努克,我都没能找到吃Kiviak的地方。我去海鲜市场买了一块海豹肉,放在烤箱里烤了半个小时后,腥味覆盖了整个房间。在那之后,我再也没有尝试因纽特传统美食。我逡巡于各家泰餐馆,把菜单上的雪蟹炒饭、泰式炒面、咖喱鸡肉、冬阴功汤点了个遍。
是的,我查询地图发现,只有一万多人口的努克至少有6家泰餐馆,而只有四千人口的伊卢利萨特至少有3家泰餐馆。经营这些泰餐馆的,是格陵兰的前两大移民群体——菲律宾人和泰国人。据格陵兰统计局数据,2024年,格陵兰的菲律宾和泰国移民合计达一千多人,在一个仅有五万多人的岛上占人口的2%。
在一家名为“暹罗兰花餐厅”(Siam Orchid Restaurant)的泰餐馆,我一边啃着炒饭里的雪蟹腿,一边听着五十多岁的老板娘讲述她的故事:她来自泰国的一个农村,后来去曼谷打工,偶然得知皇家格陵兰公司要招聘海鲜处理工,工资比泰国高10倍,诱人的收入击败了对苦寒之地的恐惧,让她义无反顾地来到了格陵兰。后来的故事跟华人在其他国家的闯荡史类似:她辛苦工作七八年,攒下一笔钱并拿到永居,开了这家饭店,还把不少村里的亲戚带来了格陵兰。
相比之下,这里的中国人并不多。2024年的统计数字显示,在格陵兰定居的中国人仅有65人。在我的旅程中,没有见到一个定居当地的中国人,没有在努克和伊卢利萨特查到任何一家中餐馆。所有与中国人相关的只有传说:格陵兰大学以前有个中国留学生,后来回国了;格陵兰政府以前有个华人公务员,后来去丹麦了;极地海产公司有几个中国工人,后来去欧洲了……中国人到哪里都能扎根的定律,在格陵兰好像失效了。
不过另一方面,中国却是格陵兰的“大金主”——是格陵兰海产品的最大买家之一。海产品是格陵兰的支柱产业,每年产值占GDP的25%左右,海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更是高达90%以上(也可见矿业有多么不给力)。其中约四分之一的海产品都会销往万里之外的中国。2021年,格陵兰政府特意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,向中国消费者推介海产品和旅游观光资源。
在离开努克的前一天晚上,我又一次看到了美丽的北极光。看着不停旋转变幻的绿光,我不禁在想,这片北极天空下的冰雪王国未来会走向何方?是继续留在丹麦,还是会投入美国的怀抱?沉睡在亿万年冰盖下的丰富矿藏,如果被开发出来,对这片净土到底是福音,还是灾难?
我没有答案。不过,想起当天下午,与一块晶莹剔透、高达四五米的海冰合影后,我走进一家纪念品店,花500元人民币买了一根海象牙做的小项链。店主结完账,跟我说:“你们中国人有钱,多来格陵兰旅游,多买点我们的东西,多买点海象牙、海豹皮,多买点海产品。我们有了钱,就有了独立的底气。”